伊拉克的天空

4 月 11 日,人们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参加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
文/《环球》杂志记者李军(发自巴格达)
编辑/胡艳芬
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夏季向来灼人,6月的最高气温已逼近50摄氏度。但今年的高温裹挟着的不只是热浪,还有街头游行人群的怒火。空气中弥漫着焦灼不安,仿佛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酝酿。
作为一名常驻伊拉克的记者,我亲历了这个国家如何在内外部势力的拉扯下艰难维持平衡。而这一次,以色列对伊朗发动“先发制人”袭击,以及伊拉克领空被用作袭击通道的事实,再次点燃了民众的愤怒。示威者的呐喊、政府的抗议、民兵组织的威胁,以及美军基地的戒备,交织成一幅充满张力的画面。
伊拉克的天空,本应属于伊拉克人,但如今,它似乎成了他国博弈的战场。在这片曾经孕育过人类最早文明之一的沃土上,人们渴望的不过是和平与尊严,却不得不一次次面对外部势力的干预与侵犯。
关闭的领空
6月13日凌晨,以色列突然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袭击,而伊拉克的天空,成了这场袭击的“走廊”。
伊拉克政府迅速作出反应——关闭领空。所有商业航班停飞,城市上空变得异常安静。然而,这种寂静背后隐藏着压抑和恐惧,仿佛整个城市都在屏息等待未知的命运。
冲突期间,至少数十架以色列战机呼啸着穿越伊拉克领空,直奔伊朗。伊拉克当局向联合国安理会递交了抗议信,并多次发表声明对以色列侵犯领空行为表达强烈谴责,称此举公然侵犯伊拉克主权,违反了国际法和《联合国宪章》。
关闭领空对伊拉克而言显然是无奈之举,却也成了“家常便饭”。就在去年4月,以色列袭击了伊朗驻叙利亚使馆,双方爆发冲突后,伊拉克出于安全考虑,也短暂关闭了领空。这种反复的领空关闭给伊拉克本就脆弱的经济带来了不小的打击。
在巴格达街头,我与一位当地老者攀谈,他说:“真正让人害怕的不是航班停飞本身,而是我们国家的天空,竟然像没有篱笆的后院一样,被别国随意穿越。”
我能理解这种心情。对于历经战乱与冲突的伊拉克人来说,“主权”从来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。它可能意味着你能否放心让孩子上下学,能否在黄昏坐在街头茶馆,是否需要不时担心有无人机从头顶飞过。
在巴格达市中心,我搭乘了一辆老旧的出租车。司机叫萨达,50多岁,戴一顶褪色的棒球帽。“我们不想再看到自己的天空被外国军机划破,不想再听到导弹掠过头顶的声音。我们已经失去了太多。”说完这句话后,他陷入长时间的沉默。我点点头,久久无言。城市的天空依旧明亮,但压在头顶的那种沉重,却是如此清晰。
在我熟识的一位学者朋友看来,这种关闭是不得已的防御姿态。而对普通民众而言,这就是不安的信号。
愤怒的民众
6月中旬以来,巴格达和伊拉克多地连续多日爆发数轮游行示威活动。
巴格达的街头,示威者的怒吼声震耳欲聋。人群如潮水般涌动,有人挥舞伊朗国旗,有人高举反美反以标语,还有人点燃了美国和以色列的国旗,跳动的火焰映照着一张张愤怒的面孔。
以色列6月13日凌晨对伊朗发动的空袭似乎并非毫无预兆。6月11日,美国国务院突然要求驻伊拉克大使馆非必要人员及家属立即撤离。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肯尼迪中心一场活动中说,安排非必要人员从中东撤离,“因为这可能是危险的地方”。
尽管美国在以色列空袭后声称未参与行动,但巴格达街头愤怒的人群似乎并不这么认为。在示威者眼中,美国与以色列始终是“一丘之貉”。这种情绪在伊拉克社会根深蒂固,源自长期以来美国在该地区的外交政策和对以色列的支持。
“你相信美国没有参与以色列的空袭吗?”一位名叫哈菲德?阿布?阿里的抗议者反问我。“他们刚撤了大使馆的人员,结果转眼伊朗就被炸了!他们明知道却不阻止,这就是共谋!”
“我们拒绝美国在该地区的存在。因为美国的存在,中东没有一天安宁的日子!”阿里情绪激动,声音已经嘶哑。
一位母亲牵着孩子站在烈日下,一边用湿毛巾擦拭孩子额头,一边对我说:“如果我们不站出来,我们的孩子将生活在没有尊严的未来。”她的眼神中流露出一种在动荡岁月中养成的倔强。
或许是担心位于巴格达“绿区”(美军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设立,位于巴格达市中心、底格里斯河西岸)的美国大使馆受到抗议人群冲击,伊拉克安全部队封锁了通往“绿区”的一座大桥,以阻止游行示威人群进入。而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遭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,近年来已是屡见不鲜。这种剑拔弩张的氛围不禁让许多伊拉克人回忆起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后的动荡岁月,担忧国家再次沦为冲突和博弈的牺牲品。
“伊拉克是个有尊严的国家,我们的天空不该成为别国战争的走廊!”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师对我说。
“世界对加沙的悲剧视而不见,黎巴嫩、叙利亚……现在战火又烧向伊朗。这场冲突若再持续下去,伊拉克或将无法置身事外。我们既担心再次成为战争的中转站,也担心战火烧进来。”他的这番话道出了许多伊拉克人的隐忧:在这个被外部势力反复撕扯、勉强维持脆弱平衡的国家,每一次地区冲突都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夜幕下的巴格达依旧闷热难耐,但游行队伍迟迟未散。不远处,荷枪实弹的军警默默地注视着这一切,他们的影子被路灯拉得很长。但他们的眼神里并无敌意,更多的是茫然与疲惫。毕竟,他们同样置身于这场风暴中。
脆弱的稳定
民众的愤怒已经从街头的游行、呐喊,升级成了武装警告。
6月15日,伊拉克什叶派武装组织“真主旅”公开威胁称,若美国介入以伊(伊朗)冲突,将“毫不犹豫”袭击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和其他利益目标。之后,伊拉克民兵组织“高贵者运动”也发出严厉警告,如果美国和以色列“胆敢动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一根头发,我们将在整个伊斯兰世界追击你们”。
我驻伊拉克工作已近两年,深知这种言论并非虚张声势。伊拉克民兵武装不仅敢说,也敢做。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,美国驻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军事基地遭遇上百次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,造成数十名美军伤亡,而绝大部分袭击都被伊拉克民兵武装“伊斯兰抵抗组织”认领。这些组织的袭击具有明确的政治意图——对美国支持以色列在加沙行动进行报复。
美军则多次在伊拉克领土对“人民动员组织”“真主旅”以及“高贵者运动”等伊拉克民兵武装发动空袭,造成数十人伤亡,其中包括平民。面对美军侵犯主权的行为,伊拉克总理苏达尼多次给美军下“逐客令”,坚决要求美军撤出伊拉克。
伊拉克要求美军撤出实际上由来已久。2020年1月,美国空袭巴格达国际机场,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“圣城旅”指挥官苏莱曼尼和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“人民动员组织”副指挥官穆汉迪斯在袭击中身亡,美国的“暗杀”行动点燃了伊朗和伊拉克国内更大的怒火。
伊拉克国民议会随即通过了有关结束外国军队驻扎的决议。近年来,伊拉克当局、民众以及民兵武装要求美国撤军的呼声不绝于耳,但执行起来步履维艰。
“我们担心如果伊拉克民兵武装这次再对美国发动攻击,伊拉克也会被卷入这场以伊(伊朗)冲突的漩涡。”萨达忧心忡忡地说。
这种剑拔弩张的气氛令人想起2003年。那个春天,我还是小学生,在电视机前目睹了美军入侵伊拉克的画面。如今20多年过去了,伊拉克仍未走出那场浩劫的阴影。
民众的焦虑不仅来自战争爆发的可能性,更在于对战争后果的担忧。冲突期间,以色列多次对伊朗核设施进行轰炸,而美国也亲自“下场”,悍然出动B-2轰炸机,投掷钻地弹,发射战斧导弹,对长期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管下运行的福尔道、纳坦兹和伊斯法罕三处伊朗核设施实施密集打击。
作为伊朗的近邻,伊拉克对袭击可能造成的核泄漏尤为担忧。因为一旦发生核泄漏,伊拉克也难逃核辐射的威胁。伊拉克总理为此紧急召开会议,敦促相关机构持续监测以伊(伊朗)冲突期间的潜在辐射风险。民众更是惴惴不安,生怕二三十年前的悲剧重演——当年美军在海湾战争和入侵伊拉克时投下数十万枚贫铀弹,导致伊拉克大部分地区先天性出生缺陷和癌症等病例激增。
“我们不想看到一代又一代孩子因为战争失去健康。”一位母亲紧蹙着眉头,对我说。
我不知道这样的未来是否会重演,但我知道,在这片因战火洗礼而变得沉默的土地上,和平的愿望从未消失。在巴格达的街头巷尾,在茶馆里人们的闲谈中,在学校教室里,人们依然怀抱着对和平生活的向往。
6月24日,以色列和伊朗达成停火协议,“12天战争”终于宣告结束,关闭了12天的伊拉克领空终于得以全部重新开放。航班恢复了,人们望向天空中飞机留下的尾迹云,长舒一口气,仿佛盼来了久违的平静。但没有人知道,这片天空的平静能维持多久。
“天空开放了,但问题真正解决了吗?”一位伊拉克民众苦笑着问我。没有人能给出答案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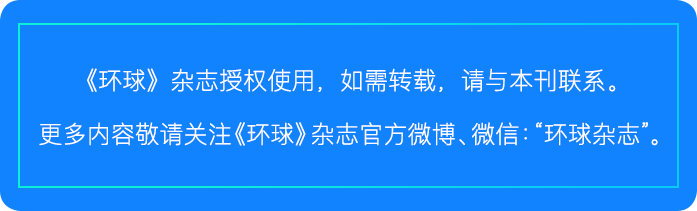

 手机版
手机版